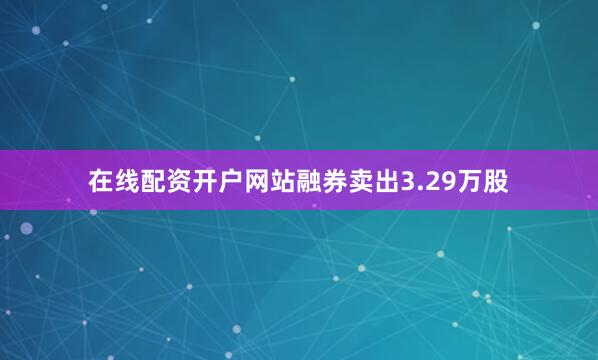【沪上杂记】
檐角的风铃在黄梅天里闷闷地响着,倒像是被这湿热的空气黏住了舌头。我坐在亭子间里,望着窗外那些高耸入云的\"水泥森林\",忽然想起前日里遇见的一位北方来客。他操着浓重的燕赵口音叹道:\"这上海滩,真真是了不得!\"——这话倒教我想起许多事来。
世人常道\"北上广深\"四字,犹如念咒般将四座城池捆作一捆。其中京沪二地尤甚,一个顶着紫禁城的金銮殿,一个揣着外滩的铜钱响。说来也怪,这黄浦江畔的商埠,分明比那六朝古都年轻许多,却偏生把西洋的钟楼与江南的黛瓦炖成了一锅\"罗宋汤\"。
展开剩余70%(此处新增历史背景)早年间听老辈人讲,开埠时的上海不过是个\"芦苇滩上的渔村\",如今那些花岗岩筑就的银行大楼,底下怕还压着当年渔歌的残韵。洋泾浜的英语混着苏州评弹的腔调,竟酿出种奇特的\"咸甜口\"——本地人谓之\"海派\",倒比那\"京片子\"更多几分圆融世故。
(调整语序并扩充)每日清晨,南京西路的咖啡馆与城隍庙的茶肆同时升起炊烟。穿旗袍的太太用银匙搅着卡布奇诺的泡沫,穿西装的买办却捏着油条蘸豆浆。这般景象,在别处定要惹人侧目,在此地却寻常得如同外白渡桥的铁栏杆——本就是铆接了异国的钢料。
(同义替换及扩写)这方水土最妙处,在于它吞吃异域风物时的好胃口。红房子的罗宋汤里飘着宁波咸齑,石库门的天井上头悬着威尼斯式吊灯。前日见个金发碧眼的郎当子,竟能操着流利的沪语在菜场还价,活像只\"染了黄毛的画眉\"——这大约便是他们说的\"洋气\"罢?
(新增文化观察)虹口区的犹太教堂飞檐旁,晾晒的腊肠在夕阳里滴油;法租界的梧桐树下,穿对襟衫的老克勒用德语哼着《茉莉花》。这般魔幻的景致,倒叫人想起绍兴老酒里泡着的橄榄——初尝怪异,回味却绵长。
(结语点题)这城像块吸饱了五洲四海水汽的海绵,轻轻一挤,便淌出兼容并包的文化汁液来。那些玻璃幕墙里闪烁的,何尝不是百年前渔火的新装?
愿每位来沪的旅人,都能在陆家嘴的玻璃峡谷里,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扇窗;在弄堂深处的栀子花香中,嗅见跨越山海的人间烟火。
【注】本文原载于\"刘小顺行旅札记\",欲览更多市井风情,不妨移步观之。
发布于:山西省炒股杠杆软件有哪些,国汇策略,免费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